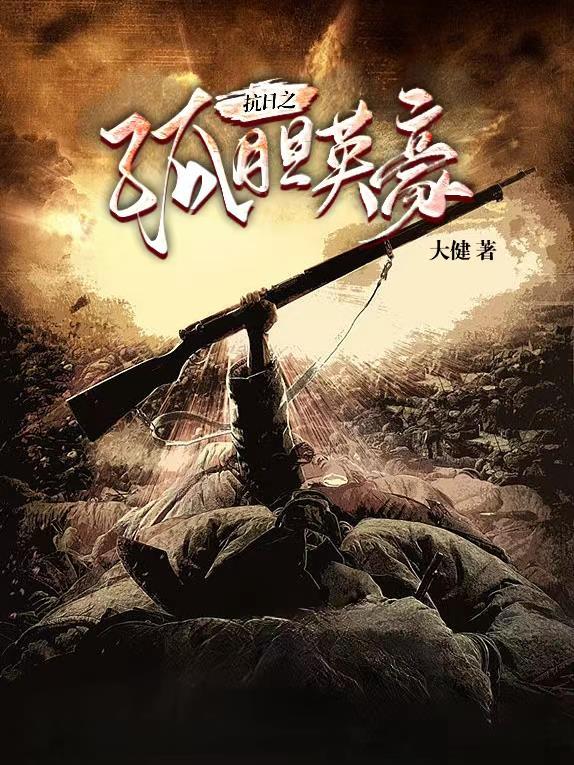911小说阅读网>四合如意 > 第283章 热卖(第1页)
第283章 热卖(第1页)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,无论是韩泗还是沈中官都只能站在那里任由摆布。
韩泗向外面看了一眼,天寒地冻,但大名府的百姓好似一点都不怕冷,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过来,半点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还是王晏开口说话,周围才重新安静下来。
王晏看向智远大师:“宝德寺捐出佛炭秘方,收留流民,朝廷赐予宝德寺粮种以示嘉奖。”
众僧人立即行佛礼。
王晏说完话,就有隶卒将粮种搬入院中,这样的举动又一次引来百姓的围观和议论。
“寺中僧人为朝廷省下供养田,本官回京之后,还会写劄子禀告朝廷,若是大梁佛寺都能如此,就可以留给百姓更多田亩,何尝不是功德一件?”
大殿上几个高僧,听到这里脸色都是一变,他们好像听到了话外弦音。
他们所在的寺庙与宝德寺不同,不但供养田足额,而且还有贩卖度牒的情形,朝廷若是真的查下来,恐怕要被惩戒。
他们回去之后,要与主持商议,要么借着宝德寺的风,捐出一些僧田,如此一来也能躲过这一劫。
王晏说完这些,算是了结了公事,然后他看向谢玉琰:“朝廷为榷场选瓷器是一桩大事,既然朝廷看中了你们瓷窑的瓷器,大娘子要仔细督办此事。”
韩泗捏紧了手,王晏当众说这些,算是落锤定音。
谢大娘子定是贿赂了王晏,这才让王晏为她说话,这样思量着韩泗仔细查看王晏的神情,想要从中看出些蹊跷。
但王晏一直神情淡然,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,看向谢大娘子时,同样带着几分威严和疏离,让韩泗恍然觉得,自己是多想了。
以王晏的出身和名声,该不会贪图那点贿赂。
难道今日的一切真的就是巧合?
“大人放心,我们定然不会怠慢,”说到这里,谢玉琰又看向韩泗,“我们刚刚建起新窑,还有许多事想要请教行老。”
在王晏的目光之下,韩泗不敢推脱:“本该如此,若有能帮上忙的,定不会推脱。”
沈中官一脸笑容,反正这些都是韩泗说的,与他没有关系。
谢玉琰又看向智远大师。
智远心中叹息,不得不向沈中官道:“寺中有禅房,若是几位愿意,可以在此逗留。”
沈中官眼睛一亮,他自然是再愿意不过,去年刚过世的那位大押班,就是在离开皇城之后,去了寺中修行,最终圆寂的时候没有任何苦痛。他听说寺中僧人说,大押班已经修成正果。他们这样的阉人不能传宗接代,只想着最后能有个好一点的结果,他盼着将来也能与那大押班一样参禅悟道。
沈中官立即行佛礼:“大师这样说,那我便不客气了。”
韩泗登时焦急:“中官大人,咱们还有差事在身。”
“还有时间,”沈中官道,“我们只要二月底之前赶回即可,刚好这些日子你好好指点瓷窑,莫要出纰漏。”
沈中官不走,韩泗也就只能留在大名府,本想着从这里离开去往他处,现在却好似被人拉住了一条腿,挣脱不得。
这不像个寺庙,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贼窝,不但要了人家银钱,还要将人也留下,恨不得将人扒个精光。
智远大师亲自引沈中官前去禅房,一同前去的还有几位高僧,沈中官心中激动,庆幸今日没有错过这场法事。
韩泗忽然有种孤立无援的感觉,他却不能去追沈中官,沈中官住在寺中不会被弹劾,他却不一定了。
他是这桩事中被压在最下面的人,但凡有个差错,他都别想逃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