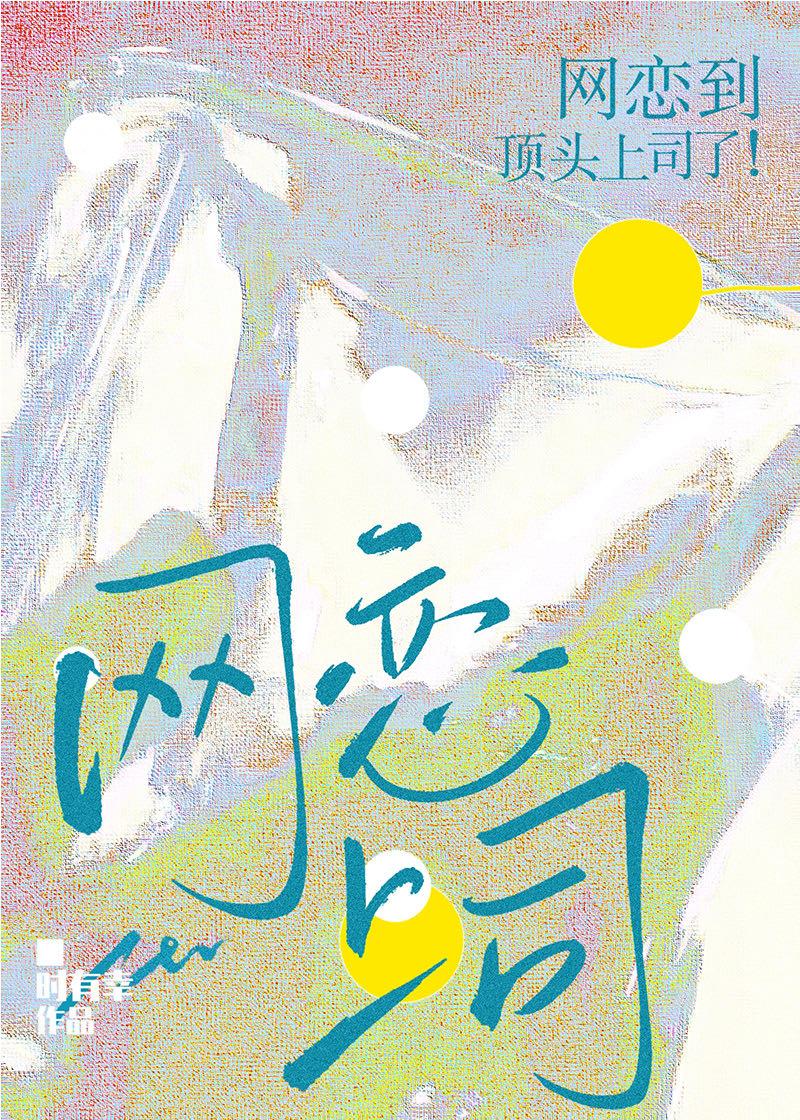911小说阅读网>穿越后医毒双全我成了大佬 > 第125章 你说扯不扯(第2页)
第125章 你说扯不扯(第2页)
尽管已经过了半个多月了,可对上戚月这张卸掉了所有伪装的脸,她还是控制不住的惊艳。
她还问过戚月,为什么要往脸上画那么丑的胎记。得到的回答是刚开始胎记是真的,后来用药消退了,为免多费口舌解释,才继续伪装的。
用的药戚月也都告诉她了,说来也是神奇,那么严重的胎记竟用了月余就全消了,只是在眼角留下一点痕迹,除了平添了美感外,没有任何影响。
“姐……咳,哥,”钟秀秀有些别扭地开口,“我们赶了这么久的路,都没怎么休息,这次也不停一停吗?”
戚月刻意压沉了声音缓缓道:“荆棘县人口多,我们可以停一停。这些天我们经过的地方偶尔也能遇到服食那东西的病患,进了城只怕会更多。”
钟秀秀赞同地点了点头,小声道:“真可怕呀,他们好多都死到临头了还不肯戒掉……”
宋心竹淡淡地笑了下,若有所思地说:“贪图享乐,必不会长久,他们既然选了这条路,就该承受相应的代价。”
戚月满是赞许地看向她,“不错啊,心竹,觉悟很高!”
“师父说笑了。”
被叫了一路的师父,戚月还是有些不自在。
当初就说了戚月没比她大多少,她教宋心竹会跟教钟秀秀一样,不用非得拜师。
可宋心竹还是敬了拜师茶,还恭恭敬敬磕了头,戚月拦都拦不住。
如今这辈分就很乱。
钟秀秀平时叫戚月姐姐,跟宋心竹也是整日姐妹相称。可宋心竹叫戚月师父,至于宋心竹那个女儿日后若是会说话,要叫戚月一声师祖。年纪轻轻的,就是师祖辈的人了,你说扯不扯。
更扯的大概是,宋心竹的女儿明明比钱钱早生几个时辰,却要叫他一声小师叔。
宋心竹的女儿跟了母姓,叫遂遂,说是希望孩子以后事事都如愿遂心。
戚月看了看外面的天色,又看向宋心竹,小声问:“你怎么样?还疼吗?”
宋心竹按了按小腹,脸色虽有些难看,但照刚才缓和了不少,“吃了师父给的药,已经好多了。”
戚月点点头,耐心跟她解释着:“你是颠簸了一路,加上生产后第一次来,难受一些也正常,你要是歇够了我们就抓紧进城找地方落脚,然后你再好好休息。”
宋心竹点点头。
戚月便扔下几个铜板,收拾好东西先装上马车。
这一路走得并不快,中途还因为好几个病人逗留过,倒也没把这匹马累坏。
戚月摸了摸马头,这些天的相处下来它也认得戚月了,老老实实地低头让摸,甚至还用鼻子拱了拱戚月的手心。
戚月莞尔一笑,思绪不受控地分散开,再重新聚拢出一个身影。
说起来这匹马还是那人挑的,也不知道他如何了。她这么一走了之,那人会不会迁怒到刘叔他们头上?
应该不至于吧?她都把解极乐丹的方子交出去了,诚意够足了,他那么大一男人,应该不会为难两个老人吧?
反应过来时,戚月简直忍不住想敲自己的头。
你怎么回事戚月?!好好的想他做什么?走都走了,他甚至都没来追,显然是默认了大家桥归桥路归路啊!这不是你希望的吗?
去父留子,去父留子啊戚月!
做完了心理建设,钟秀秀他们也都坐上了马车,戚月赶紧收回思绪,颇娴熟地赶起了马车。
伴随着车轮碾过路面的响声的,是一阵清脆的铃铛声。
马车内,钟秀秀低头看着戚楌乐呵呵的模样,不由也笑了,抬头跟宋心竹道:“我现了,最近几天钱钱一听见医铃响就笑,还要去够呢你看。”
宋心竹看了过去,不禁也笑了,语气颇有些感慨道:“说来钱钱与遂遂同天出生,遂遂到现在还没怎么笑过呢,钱钱倒是个爱笑的。”
两人说着话,马车突然停了下来,钟秀秀掀开车帘往外一看,缩回来道:“又来个听见医铃声出来寻医的。”
两人都下了马车,见来的是个瘦骨嶙峋还有些驼背的老者,仿佛站着都很吃力,张口却是求他们救救他的老伴儿。
“我老伴儿咳了有些日子了,这段时间更是频频咳血,去县里开了不少药,可都没有用,白白花了不少银子……”老者说着,忍不住朝紧闭的马车门张望,又问:“大夫可是还在车里没下来?能否跟我去给我老伴儿看看?”
戚月上前一步,道:“老人家,我就是大夫,这两个都是我的徒弟,若您信得过,可以带我去看看。”
听了这话,老者明显有些犹豫,目光在戚月身上来来回回地打量着,显然是不相信这么年轻的大夫能有什么能耐。
再看看戚月身后,一个大夫,带着两个女徒弟,还都带着孩子,怎么看怎么不正经。
老者:“……”
戚月也不催,一路上这样的表情她看过不少了,全凭他们自愿,若是信不过,他们直接走人就是,左右都没甚大碍。
良久,老者琢磨够了,叹了口气道:“罢了罢了!反正也没有别的法子了,就让你试试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