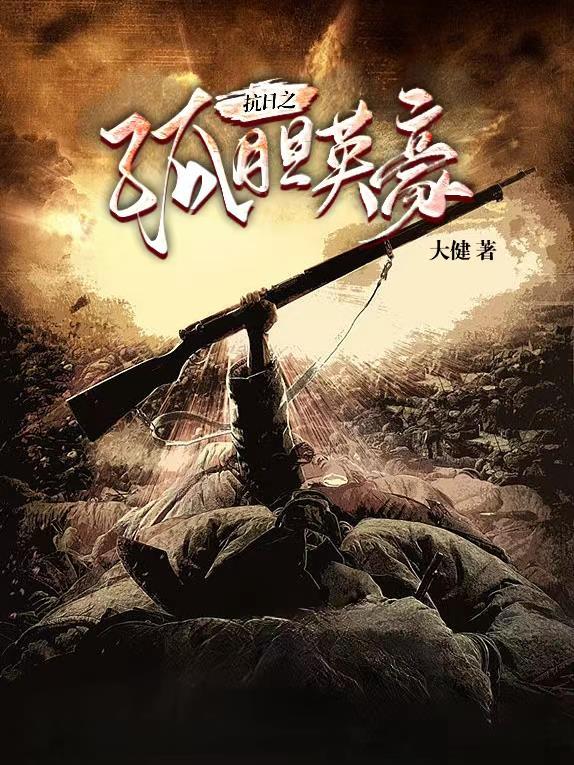911小说阅读网>穿越后医毒双全我成了大佬 > 第49章 打架也要讲究方法(第1页)
第49章 打架也要讲究方法(第1页)
卖马的贩子见到喻晨便迎了上来,他看看喻晨手里多得都快拿不住的东西,又看看戚月的肚子,道:“你那板车我帮你套上了,这马脚程快,你这又是载人又是拉东西的,就受累牵着回去吧。”
喻晨点头道了声“多谢”,从贩子手里接过了缰绳,而后让戚月和钟秀秀都上车,自己牵着马不紧不慢地往回走。
戚月不禁干笑道:“这两天辛苦你了哈。”这都来来回回的走了几趟了。
喻晨不语,钟秀秀就在旁边捂着嘴偷乐,被戚月给了一板栗,笑得更开心了。
路上,戚月简单把遇到卖鱼妇人以及她的请求告诉了喻晨。
喻晨听了也只是说了声“知道了”,对戚月时不时要给人诊病的事接受良好。
戚月就坐在板车上看着黑马呆。
这马看着精力十分旺盛似的,出了城走在宽阔的大道上就有点收不住步子,几次想跑,都被喻晨看似随意地扯了下缰绳,就猛然缓步,气得一路都在不耐烦地打响鼻。
三人一马进村时,正看见老赵媳妇和徐婆子坐在村口老树底下歇脚,看样子是刚从河边洗完衣服回来的,见喻晨牵着这么高的一匹马进村,都忍不住凑上来打听。
“呦!喻秀才,你们这是从县里回来?”赵大婶一贯好信儿,“你们最近是真的财了呀,隔三差五就往县里跑,这马也是买的?”
喻晨并不言语,只微微颔便打算走。
徐婆子看看稳稳当当坐在板车上还带着个幂篱的戚月,见她丝毫没有想要理人的意思,不由有些不悦,酸唧唧地在旁道:“那必然是赚了大钱了,看看戚丫头那傲气的,见了长辈都不说话的。”
戚月丝毫不为所动。
赵大婶一阵嗤笑,“徐家婶子,这你就不懂了,人家现在可是县衙承认的立了大功的能人,县里到处都贴着她的画像呢。”
这还是他家老赵赶骡车进城回来同她讲的,村里闻名的傻子野种一夕之间成了了不得的大人物,无论怎么想都是一件让人十分不舒服的事。
就在刚才,她还在跟徐婆子说起这事,话里话外都是质疑。徐婆子当然也是不肯相信,两人一拍即合原地编排了半天,这会儿突然见着人,自然是不肯就这么轻易放她走。
徐婆子道:“那就怪不得了,县衙肯定奖赏了不少银钱吧?也不知道戚家这祖坟上是冒了什么烟,竟让这么个小丫头抛头露脸的,真是有伤风化。”
“就是,这要是在我们家,哪能容得了女人这么显摆的?”赵大婶满是鄙夷地补刀。
戚月像是被念得犯了,冷冷地问了句:“二位是把卖盐的打死了么?怎么都这么闲呢?”
徐婆子一噎,满是褶子的脸上泛起一抹红,赵大婶却不在乎那点儿脸皮,闻言声音更加尖利了,“戚丫头,你这话说得也忒没教养了。好歹我跟徐家婶子都是你的长辈,你娘就是这么教你跟长辈说话的?”
说到这,赵大婶故作恍然地补道:“哦!你瞧我这记性,你根本没娘教。”
话落,她和徐婆子都笑了,眼里尽是嘲弄。
有什么可神气的,再威风,不也是她那早死的娘留下的小野种么,连爹是谁都说不清,还在这里装模作样个什么劲儿。
钟秀秀听了这些话,气得直抖,想也没想就跳下板车,随手抄起路边的枯枝冲了上去。“你们两个老不死的都放的什么屁!快滚!再不滚我抽死你们!”
赵大婶哪里会被个见都没见过的小丫头唬住,上去就扯住了她扬下来的枯枝,嘴里不客气地骂道:“你又是哪里来的小蹄子?这有你什么事?果然跟着戚月那小贱人的都是一个东西,一点教养都没有。”
“你……”钟秀秀气得红了眼。
就听戚月在后头十分淡然道:“秀秀,过来。”
回头,就见她不知什么时候从板车上下来,淡定地朝喻晨摆摆手示意他别动,自己走到赵大婶面前,颇平静对她道:“道歉。”
赵大婶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,“你做梦呢?凭什么要我给你道……”
话没说完,一记清脆的耳光猝不及防扇在左半张脸上,赵大婶直接被打蒙了,捂着脸愣愣地看着戚月。
戚月重复道:“道歉。”
这下赵大婶反应了过来,顿时气血上涌厉声尖叫起来:“好你个小贱人!竟然还敢打我,看我不……啊!”
她一记耳光被戚月轻巧躲过,又被戚月反手一巴掌扇在了右脸。徐婆子在旁都看傻了,似乎做梦都没料到一向被戚家媳妇欺负得屁都不敢放的戚月,如今居然会如此泼辣,话没说两句居然就直接上手了?
赵大婶已经疯了,双目赤红地扑了上来,抬脚就要踢戚月的肚子,可腿刚抬起来,就觉头皮一阵剧痛,不由自主地向后仰去,继而才难以置信地觉,自己的头被戚月扯住了。
钟秀秀在旁看得心惊肉跳的,生怕对方一个不小心碰到戚月的肚子,可戚月分明轻松得很,眼见着赵大婶几次胡乱扑棱都要碰到她肚子了,可就是能被她轻巧躲过。
戚月甚至还扭头看向钟秀秀,气定神闲道:“看到没?打架也要讲究方法,像你那样一味猛冲,很容易挨打的。”
喻晨:“……”你也并没有多么讲究。
钟秀秀张大了嘴巴。
戚月回头,幂篱遮盖下的面上丝毫没有起伏,谁也没看清她做了什么,就听赵大婶突然“嗷”的一声尖叫,倒在地上痛苦不堪地打起滚来。
钟秀秀见了第一反应就是昨日姐姐用过的那个什么万蚁噬,可她一直紧盯着,这里也没有水给姐姐泼,她是怎么做到的?
很快,钟秀秀就现了不对,那个大婶不像昨天那些人一样,在身上又抓又挠的,只是很痛苦地捂着心口,脸色惨白惨白的。
戚月拿下了幂篱,眼里一片冰冷地又重复了一句:“道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