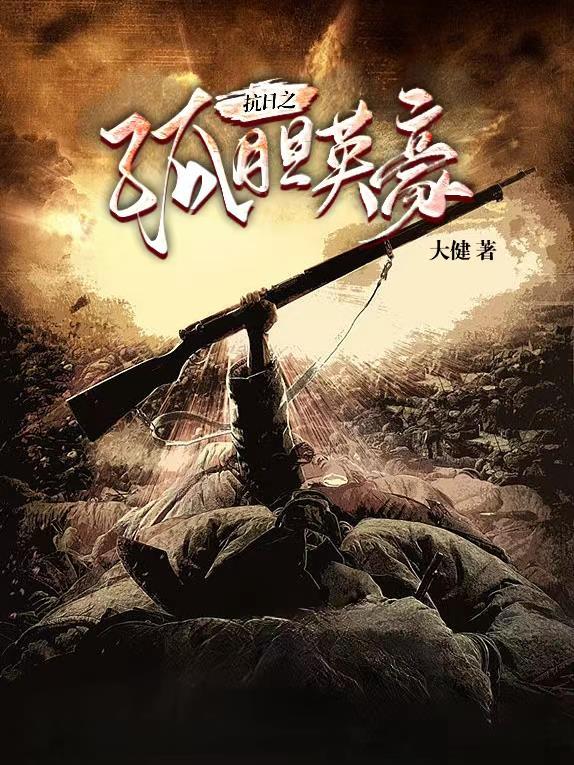911小说阅读网>明朝秦淮河畔 > 第3章 纷繁叠错 长夜心娆(第3页)
第3章 纷繁叠错 长夜心娆(第3页)
三人撞破窗户而去。
三人踩在房檐的琉璃瓦上,碎步移动。
突然,院中亮起无数火把,星星点点的火把亮光,很快连成了片。
同时,数十个亮银箭头对准了景文三人,当三人缓过神来,为时已晚。
程不悔扭头看房内,在窗户口伸出数支长。
苏青青拥着惜婷坐在床上,身边站着的正是马鹏。
房中持枪家丁不下十人,想冲回去也万难了。
马鹏双手背后,阴阳怪气道:“呦,景少爷,你什么时候学成的攀檐上梁的功夫啊,我家房檐小,您要有个什么闪失,我可承担不起”。
景文怒不可遏,欲动手,被程不悔拦下。
马鹏冷哼一声,:“你们是自己下去,还是我帮你们下去”。
苏青青急道:“父亲,不可!”。
马鹏不理,一挥手,数支长枪刺向三人腰间。
忽然,一条白绢垂了下来,程不悔见白绢不足三寸宽,眼疾手快将景、莱二人推向白。
二人顺势抓住白绢滑下阁楼,同时,程不悔一跃而下。
马鹏大惊,派家丁上房查看。
不想,白绢撑了一段距离,还是从中间断开。
还好二人已到一楼房檐,摔下才无大碍。
不过二人尚未起身便被擒下,程不悔刚落地,三柄刚刀已突至胸前。
擒住三人者,正是奉浉。
奉浉对身边人耳语一番后,三人已被五花大绑押到奉浉面前。
奉浉扬起手中的马鞭,作势要打。
景文后仰欲躲,奉浉笑了笑,收回了马鞭。
莱博瞪目怒斥,只骂出两个字,即被破布堵了嘴。
程不悔奈何被侍卫压着,动弹不得。
奉浉轻蔑道:“不打你是怕脏我马鞭”,一挥手,三人被蒙上眼睛压了下去。
搜寻了半天,没找到半个人影。
气急败坏的马鹏,大骂家丁无能,但也无可奈何。
马鹏安排了留守的家丁后,来到后院。
奉浉的三十多骠骑整装待,马鹏穿过群骑,看到奉浉拿着酒袋独饮。
马鹏走上前去,曲身问道:“大人,您几时出,小的略备了些酒水,为您和弟兄们饯行”。
奉浉饮了口酒道:“什么人扔的白绢你可查出”。
马鹏愤愤的说:“没找到,要让我逮住他,非让他好看”。
奉浉嗯了一声,心想:今晚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没逃出我的眼睛,那抛白绢的紫衫女子也被我看的清楚”。
“只是目前不清楚她的底细,先掌握她的行踪再说。
马鹏见奉浉不语,以为要责罚自己办事不利,刚想辩解。
奉浉道:“你去请苏姑娘下来,转告姑娘不用收拾物件,府中已备齐全。记住,是请!”。
马鹏嘘了口气,转身离去。
青青的琴房中,惜婷细细的照料着炭火。
苏青青坐在琴前,抚摸着琴面,一遍一遍。
这一夜,哭也哭了,闹也闹了,虽然不是自己闹得,但总也跟自己有关。
悲伤,惊惧,忧思一股脑的倾泻在自己身上。
哪怕是个男子多半也难以招架,何况我这一介女流。
青青手指划过琴头的梅花断,自从爹爹去世以后,我再难言欢笑。
每每梦中见到父亲,恨不能握着爹爹的手,永不分离。
梦醒后,枕巾早已沁湿。
青青掌心掠过琴腰的雪竹断,来到这里的第三年,头次来到舞房,被打到半死。